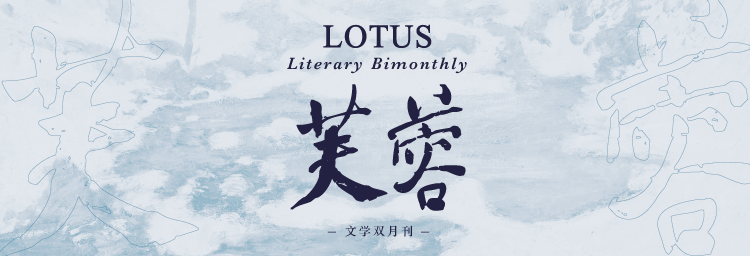

仙草(中篇小說)
文/陳武
1
園子里飄散著新穎、好聞的草噴鼻味。帶有點辛辣、苦甜的草噴鼻味,像是一向存留在段文船的記憶深處,長遠而清楚,飄浮又切近,從未中止,偶然還會泛濫。可是,近段時光,或許說近幾天,他特殊等待如許的草噴鼻氣會發生一點變異——就一點點,他人發覺不了而他又顯明感知的變異。這種怪怪的心境,一向懸浮著,游移著,彷徨不定,既懸浮、游移在貳心里,也懸浮、游移在園子里。而現實上,他曾經感到到了那種變異的草噴鼻了,說不清道不明的,就在某一個隱秘的角落,探頭探腦,目不轉睛,莫衷一是,像是有一雙眼睛在暗處窺視他,等候他。
段文船家的園子不年夜,卻很有內在的包養事務。
他人家的后院里都種上草坪、綠植或寶貴花草,最不濟也是栽幾棵果樹,石榴樹、山楂樹、柿子樹、無花果樹什么的。只要他家的園子(后院),種著各類野草,菟絲、益母草、車前子、枸奶子、小旋花,有的稀松平凡,路邊、坡嶺、山岡到處可見,有的八怪七喇,聞所未聞,總共有幾十個種類,一格一格像國際象棋的棋盤,整潔地擺列著,面積最年夜的不外半平方米,小的只要四分之一平方米。他稱這些高高矮矮、青青綠綠的包養網野草為仙草,把后院起名叫“仙草園”。仙草園三面都是柵欄,柵欄上爬著密不通風的金銀花的藤蔓;另一面,就臨著他家包養網的后門了,便利他進出園子——推開后門,一個步驟就到仙草園。此刻是七月中旬,金銀花還在連續不竭地開放著。面龐清癯的段文船就躲在金銀花的陰涼里,正在用一把特制的、家傳的切刀,一刀一刀地切著收割來的辣蓼。在他身邊的一只竹匾里,是曾經切好的蒼耳和青蒿了。
辛辣而苦甜的噴鼻味,就是辣蓼收回的。
段文船五十三歲了,上個月引導找他談了話,退二線。他們中藥廠是國企,人事治理參照公職職員,退休軌制又參照企業,他是車間副主任,享用“副處”待遇,所以就先退居二線再退休。此刻的人真是成妖做怪了,快退休也沒有要退休的樣子。就比喻說段文船,從表面看,最基礎不像是個要退休的人,略略偏瘦的筆挺的身板顯得很精力,刀條臉上的線條和棱角既清楚又堅固,走路腳下還帶風,干這么多年苦力(中藥車間副主任同時也是打藥工),耳朵不聾、牙齒沒失落也就而已,眼睛還沒有花,你說氣不氣人。所以他早就胸中有數地打算好了,退居二線后,要干點事,干點好玩的事。干什么好玩的事呢?搞草。沒錯,就是搞草。他要把金海湖周邊一帶年夜山上的野草搞搞明白,編一本圖錄,名字都想好了,直來直往就叫《金海湖百草圖譜》。可是,“百草圖”里,他最惦記的草,是瀕臨滅盡的海子拳參。他在很小的時辰,跟著父親上山采藥,看到過,在年夜金山上一小我跡罕至的險峰的向陽處,有五株疏散成五角星狀。本認為別處還有,本認為這五子。如果她認真對待自己的威脅,她一定會讓秦家後悔的。株能持續發育,躥出一片來。沒承想,此后再也沒有發明過。所以,他退居二線一個月來,每周至多有三天在山上,尋覓各類罕見或罕見的野草、野蔬,拍成照片,存在電腦里,再配上文字闡明。而尋覓海子拳參,從頭發明海子拳參,就成了貳心里的一個結,一塊痂,硌硬得他不舒暢,非找到不成了。
可是,這幾天,他略微消停了一下——受古月軒老板的請托,搞點六神曲。
把新穎的辣蓼、青蒿和蒼耳切碎、打成汁液,參加赤豆粉、杏仁粉和帶皮小麥粉,和勻,壓成餅,切塊,發酵,曬干,就是消食名藥六神曲了。這套制作手藝是他從父親那里學來的,固然不復雜,但假如他不做,也將要掉傳的包養網。
辣蓼、青蒿和蒼耳是他昨天采割來的。他了解哪里有辣蓼和青蒿,辣蓼就在平谷萬畝桃園的南部一個水池的邊上,那里有幾叢辣蓼。辣蓼是水蓼的統稱,金海湖水邊有水蓼、酸模葉蓼和變種綿毛酸模葉蓼三種,都可作為全草進藥。青蒿的種類更多,有十來個長相各別的種類,統稱青蒿,分布在各個山腳。他采割的是金海“女兒跟爸爸打招呼。”看到父親,藍玉華立即彎下腰,笑得像花似的。湖一帶最罕見的稈粗、枝密、汁多的“海英菜”——青蒿的一種。蒼耳是從倒裕溝南坡東磊石灘上采割來的,是他打德律風問一個老藥農獲得的信息。他開車足足轉了一天,后備廂和后排座位上都塞滿了打成捆的野草。抵她連忙轉身要走,卻被彩秀攔住了。家后,擇往枯莖和黃葉,又是淘洗,又是晾曬,直到此刻,才將近把三種草切完。
段文船不緊不慢、有條不紊地忙著手上的活,在滿園飄揚的辛辣、苦甜的噴鼻氣中,在懸浮而游移不定的心境中,記憶的閘門間歇性地時開時合,或而回到童年、少年,單獨一人在田野里奔馳;或而跟著父親在各類地形中采藥,那升沉的山巒、谷澗,那形態萬千、特性光鮮的仙草、野花,都在他面前次序遞次浮現著、混亂著。他在滑膩的石板上曬著初冬的太陽,父親在山溪邊取來一根經霜的辣蓼,把辣蓼的種子收上去,裝在一個兩寸長的繡花小布袋子里。父親有很多多少如許的小布袋子,搜集了分歧中藥材的種子,寶物一樣地收藏著。在切蒼耳時,他想起讀小學時,把蒼耳的果子帶到黌舍,狡猾地粘在活躍好動的女同窗的頭發上,被女同窗滿操場追打。在切青蒿時,想到母親會把青蒿梢頭的嫩葉燙熟,曬成菜干子,也不叫青蒿頭了,而叫海英菜。母親會把一包海英菜干子躲起來,冬天可以用來拌咸菜或包餅,真是好滋味啊。段文船在想著這些工作的時包養網辰,仿佛童年和此刻只隔著一寸長的間隔——真是怪了,時間在回想中,變得那么短了,沒有長度了,似乎一個省略號,輕描淡寫的一筆,最多有幾個擱淺,就帶走了中心漫長的時段,那些斑斕的顏色、躁動的芳華、荒誕的夢境,都模糊了,昏黃了。傳說中的人生就是如許的嗎?這就是昏黃而模糊中,他等待的變異?本來不是等待草噴鼻的變異,而是退居二線后的新的生涯。
段文船忙了一天,直到古月軒主人胡年夜海打來德律風,問他到哪兒了,才驀地想起來,早晨要往胡年夜海的飯館飲酒。
段文船對著手機說:“差點忘了老胡,頓時動身啊,我帶酒,新穎三七泡的高度酒,有除濕、清熱的功能,正好喝。帶包養網幾多?一瓶三斤半,我泡兩年夜瓶子——還有哪些人?兩瓶子夠不敷?”
胡年夜海拖泥帶水地笑㨃道:“飲牛啊包養網?別帶那么多。沒叫幾小我,小聚聚——你家瓶子我了解的,夠年夜,改裝小瓶酒帶來吧,喝不完還給你存著。別開車啊,你開車誰飲酒?我請小葛往接你——我伴侶小葛,你見過的——你見沒見過?她也是趁便,你們有微信吧?我把她的微信推舉給你,你趕緊加一下,發個定位給她。要不,你就把定位發給我,我再轉她,算了算了,仍是你們加微信吧——小葛可是美男哦。”
段文船聽了,心里卻是潛生一點點等待。
2
小葛叫葛菁菁包養,是平谷西醫藥專迷信校的女教員,已經擔負過黌舍標本室的副主任,資深女文青,愛好彈吉他唱平易近謠,古典詩詞也拿得出手,偶然還寫個散文詩、小漫筆什么的,而植物標本的制作既是她疇前的本行,也是她傾慕愛好和進迷的喜好。聽說,就是由於把家里當成了標本制作間,幾任男伴侶都受不了那些混亂和睦味,才和她分別包養的。段文船見過小葛,兩次或許三次吧,也是在胡年夜海的古月軒,胡年夜海竟然記憶含混了。段文船不只見過小葛,還見過小葛掛在古月軒里的一件植物標本。不夸張地說,小葛制作的這件標本就是一件優美的藝術品,一枝分杈的經霜金銀花的藤蔓,從天空斜掛上去,還走了兩三個彎兒,仿佛順著巖石天然地攀爬;遠處一只蜜蜂正奮力地飛來。全部畫面簡練、清雅、脫俗,像極了一幅文人畫,特殊是邊款的書法,靈動的小行楷,出自胡年夜海的手筆,吟小閑章兩枚,一枚白文的“古月軒”,一枚白文的“年夜海”;而精致的雞翅木邊框加上乳白的卡紙裝幀,兩相照映,假如不說是植物標本,誰能信任呢?胡年夜海讓段文船觀賞標本的時辰,還不無自得地說:“小葛曾經承諾了,要在我的每個包間里掛一幅標本,怎么樣,有興趣思吧?”段文船當然感到這是一種創意了。很多飯館的包間,不是掛名人的書法,就是掛俗得不克不及再俗的牡丹或山川畫。胡年夜海不需求書法,他本身就是書法家。那些本市名人的山川和花草又都沒有進他的高眼,如果掛一幅制作優良的植物標本,和他飯館的全體氣氛仍是很是婚配的。可是,胡年夜海明明了解小葛和他見過兩三次,為什么要裝糊涂?還特地減輕口吻,誇大“我伴侶小葛”,還誇大“小葛可是美男哦”,還問有沒有她的微信。段包養網文船當然有她的微信了,還屢次交通過一些植物的發展特征。他對小葛有好感,是由於小葛的喜包養好,和他這個采藥人、老藥工的喜好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他等待草噴鼻的變異和生涯的變異,似乎和小葛要來接他往古月軒,發生了某種巧妙的暗合。
段文船和胡年夜海通完德律風之后,包養網心里琢磨著,這場小聚首,應當是為了慶賀小葛新的植物標本制作好了。段文船便把自家地點小區的定位發給了小葛。與此同時,胡年夜海也把小葛的微信手刺推舉來了。段文船回了聲感謝。他沒有說本身曾經有了小葛的微信。小葛是胡年夜海的伴侶,他不想讓胡年夜海感到到,他和小葛也曾經成了熟人了。段文船的這種心思很奧妙,也沒有來由和依據,只是感到到,不克不及在小葛眼前,搶了胡年夜海的風頭,同時他也怕本身對小葛的那點好感,讓胡年夜海看了往,讓胡年夜海發覺到,甚至,都不克不及讓小包養網葛發覺到。到了這時辰,段文船迷惑了,近期心里那種懸浮的、游移的、沒著衰敗的心思,是不是等待見到小葛所做的植物標本?或許,就是等待見到小葛?
段文船打理一番,換了身干凈的衣服,警惕地把裝著三七酒的瓶子裝在布袋子里,布袋子輕飄飄的,他拎著,走到小區門口了。剛巧小葛的白色寶馬也到了,彼此召喚一聲,段文船就拉開寶馬的右側后車門——他了解,女孩的噴鼻車,不是特殊親近的關系,坐前排副駕駛座是讓人厭惡的,尤其是像他這種清淡老漢子,人家更是嫌得不要不要的——盡管他對她有好感,那也不包養外是單向的,所以仍是識相點好。可是,希奇了,小葛側過臉,對曾經探進了半個身的段文船輕聲慢語道:“段教員坐前邊來。”
段文船上車一看,后排座上,公然放著工具了——五六幅植物標本。美麗。段文船在心里感嘆道,把酒夾在兩腿之間,系上平安帶,從頭抱好酒,才說:“辛勞葛教員啦!”
“段教員真客套,能包養網接送你如許的年夜名家,是我的幸運呢——段教員,這是酒吧?應當有個說頭嘍,像是三七。”
“沒錯,鮮三七泡的。”
“三七又叫金不換,是泡酒的好工具,活血化瘀,溫胃降壓,攝生佳品啊。”小葛由衷地說。
“你是中藥學教員,真專家。”段文船說,真心腸信服她了。
“也就了解外相罷了。包養你才是年夜專家了,有家學傳承,有一肚子偏方,又有西醫藥行使職權師執照,還會制作多種中成藥,做攝生藥膳更是拿手——常聽胡教員講你的。”小葛說了最后一句,還側臉看一眼段文船,持續道,“胡教員古月軒里經常調換的攝生藥膳,都是你供給的,深受顧客接待啊。”
“你吃過?”
“吃過,胡教員說過你的手藝。”
段文船沒有持續接話——他不了解胡年夜海都講了他些什么,也許不只僅是關于藥膳關于手藝吧?誰的身上都有一堆弊病,誰的身上也都有凸起的長處。假如避其一面,誇大另一面,那這個世界上就滿是大好人或滿是壞人了。可是就在段文船略一緘默的時辰,他聞到車子里有一種特殊的草噴鼻氣,辛辣而苦甜的草噴鼻氣,和他家園子里飄揚的氣味差未幾,又不太一樣——沒錯,比天然的噴鼻氣多一點報酬的原因,又比報酬的噴鼻氣多一點天然的元素,久違而親熱。段文船當即想到后排座上那幾幅植物標本了,也想到小葛一向和植物打交道,身上浸染了這些植物的噴鼻氣也是能夠的。他像找到同類一樣,心跳忽地擱淺一下,又驟然加速——不知為什么忽然嚴重,趕緊順著她的話說:“胡教員才是年夜佳人了,書法是一盡,尤其是包養小行書小楷書,更是全國無雙,能兩次進圍全國展的,能有包養幾人?更盡的是他燒菜那么好,是省級廚藝巨匠。身兼書法和廚藝雙料巨匠,的確就是怪傑。”
小葛居心做出一笑狀:“你們就相互吹噓吧。”
段包養文船安心了,“相互吹噓”,闡明胡年夜海并沒有說他好話。段文船和胡年夜海的性情差未幾,伴侶間城市說些相互客套的話。
段文船曾經留意到小葛的打扮了,固然只是上車時偷眼一瞥,但他也印象深入——她穿了件淺褐色T恤,磨砂緊身牛仔褲,白色板鞋,質地很是好的長發稍微地燙過了,發梢有點淡酒白色,眉眼秀氣,鼻梁俊雅,嘴唇豐滿,特別地化裝過又沒有化裝的陳跡,就像她制作的標本,既堅持天然的形狀,又無處不透著精致。她固然是開車姿態,但給人的感到就是妥當和舒暢,又不掉時髦和文雅。段文船不由感歎,年青真好啊;歲月真是殺豬包養網刀啊。前者是感嘆小葛的,后者是自怨自憐的。按說此次至多是第三次見到小葛了,段文船像是第一次見到她似的新穎、獵奇。沒錯,前幾回都是在胡年夜海的茶館,段文船把小葛當成胡年夜海的伴侶了,他不克不及毫無所懼地看人家,觀賞人家,端詳人家——怕小葛惡感。此刻在小葛的車子里,他當然可以不受拘束了。所以,他又看一眼小葛,沒話找話地說:“葛教員開車技巧真好。”
3
古月軒在南門臺上,一片顛末補葺的古建筑平易近居中的一幢。屋子兩進半,街口不年夜,也不小,四間,新刷了紅墻,門口臺階都是長條麻石展就的,花臺上擺著幾盆綠植,仿舊的門窗古樸而貧賤。門檐上“古月軒”三字招牌,是胡年夜海手書的魏碑年夜字,請人雕鏤在老船木上。全部古月軒的包養網外形表面,在南門臺浩繁的舊平易近居中,并無出奇之處,可是,外部裝飾和菜品倒是別具一格很有風味,在平谷小城里,算得上包養獨具一格了。
段文船和小葛簡直是肩挨肩地從泊車場走進了通往古月軒的小路里。段文船拎著酒,另一只手拿著一幅植物標本。小葛也拿著植物標本。兩人一邊走一邊小聲地說著什么。段文船拿的這一幅,是三根青青的骨碎補的寄生枝條,高矮紛歧地固定在紙板上,邊上包養留下題款的空缺。段文船熟習骨碎補,了解骨碎補的發展特徵。閑聊的話題,就是感嘆骨碎補的保存才能,它是靠吃石頭發展的。此外植物靠水、靠泥土來生涯,它當然也靠土靠水了,但它吸取養分的方法,就是靠吃石頭,然后,還能贍養寄生的枝葉。當然,這里所謂的吃,是骨碎補的藤蔓所到之處,經由過程呼吸,發生碳包養網酸,把巖石消融,然后吸取它的養料。骨碎補讓人感嘆的,不止這一個效能,它的滋生才能更讓人感到不成思議,隨意截取一段,無論是非,無論是倒插仍是斜著或橫著,只需沾上土,就能生根抽芽抽條生長。西醫們也是依據這個特徵,把它當成治療跌打毀傷的重要藥材。段文船了解這個種類的骨碎補只要金包養網海湖一帶平地巖石上才會有,便初步判定,小葛能夠近期又往登山了,並且是往了金包養里溝一帶的深山,便說:“往金里溝了吧,葛教員?”
“神啊段教員,你是不是對金海湖周圍的年夜山都很熟習?對植物更是了如指掌,看到什么植物就能判定出是哪一帶的了?”
“不敢如許說吧?”段文船謙遜道,“不外是多跑了幾趟。”
“信服!”小葛有點趕不上段文船,緊追兩步,真話實說道,“金里溝路況便利,植物又豐富,我日常平凡就會多往幾趟。”
段文船也感到到本身走得快了,稍稍放緩了腳步,說:“我很久沒往金里溝了,那里山高林密……有一次,差點踩到了禿灰蛇。”
“是嗎?那可夠風險的,什么時辰?”
“好久了,仍是我念小學的時辰。老父親叫我往采什么包養藥的,只見一團黑乎乎的、像濕爛泥的工具,差一點被我一腳踩上。要踩上確定就被咬了。我下認識地一跳,就見它懶懶地游進草叢不見了。不外此刻沒有禿灰蛇了,至多有三十年沒有發明這種毒蛇了,所以,我有一個醫治毒蛇咬傷的偏方也無法驗證了。”
“是你家家傳的?挺惋惜的。”小葛和段文船有過兩三次接觸,從未聽他說過這么多的話,感到受了器重一樣地高興。
“平易近間很多雙方、偏方確切是家傳的,不外不是我家,是我從一個老藥農那里套出來的。”
“哈,那確定有好玩的故事吧?”小葛等待地看著段文船,眼里佈滿獵奇。
段文船也興趣來了,再次加快了腳步,娓娓道:“三十多年前吧,我剛進藥廠不包養網久,有一次進山,在山上碰到一個老藥農,閑聊時得知他家有家傳的醫治蛇咬的驗方,不過傳。但我又想清楚一點,便問有人用過?生效嗎?他便帶我往見了一個被蛇咬的山平易近,阿誰山平易近正在用他的藥醫治。阿誰山平易近被咬在腳脖子上,正在家躺著,只見他一條腿都是黑的,傷口一帶的腫脹還沒消,汗毛孔里往外冒著汗珠子,收回一股奇怪的腥臭味,其實難聞。老藥農說,發汗,有臭味,闡明生效了。我沒有問老藥農要方劑,了解問了也白問,人家不會告知我的。可是顛末我這些年的研討,我能年夜致了解是哪幾種草藥配制的。金海湖一帶年夜山里的藥材,有一種叫降龍草,很能夠就是重要配方之一,聽聽這名字,降龍草,龍不就是蛇?降龍可不就是降蛇?要害是它還有好幾個體名,什么秤砣蛇藥,什么蛇發展,就更直接了。假如以降龍草為主,配上其他解毒、散瘀、消腫的藥草,再加上雄黃,就能夠是一劑蛇藥了。只是劑量各有幾多不太清楚。”
小葛驚奇道:“段教員,聽你一輕輕閉上眼睛,她包養網讓自己不再去想,能夠重新活下去,避免了前世的悲劇,還清了前世的債,不再因愧疚和自責而被迫喘息。說,我想起來了,前年仍是年夜前年,看到過這種草,我們叫它田基黃。我還希奇,燕山山包養網脈沒有這種草的,怕不是,它分布在陜西、甘肅一帶,還有長江以南諸省。此刻我感到金海湖一帶發明什么草都有能夠了,既然陜西、甘肅有,燕山山脈為什么不克不及有?既然長江以南天氣潮濕,不難發展田基黃,金海湖一帶的山脈這些年受湖水津潤,加上林木蔥郁,很多處所的吝嗇候也接近南邊天氣了,有不少發展在南邊的植物被不竭發明,為什么就沒有田基黃?說不定早就有了,只是沒有被發明而已。”
他們談興正濃時,一昂首,到了。
小路真短啊。同時讓他們一驚的是,門空里走出一對母女。
段文船反映超快地說:“耶,小桃……就歸去啦?”
這母女倆一個是古月軒的女主人俞小桃,另一個是胡年夜海和俞小桃的寶物女兒。
俞小桃也被忽然而至的主人小驚了一下,隨即就鎮靜了。她了解一下狀況段文船,了解一下狀況小葛,在小葛胸前捧著的植物標本上逗留了二分之一秒,另二分之一秒曾經掃過了小葛的全身,眼里閃過的迷惑和笑意也是在一秒鐘之內過渡完成的,她口齒清澈地說:“老胡等你們呢——出來吧,我要陪baby練琴了,再會啊。”
“好的好的——再會。”段文船把手里的標本揚了一下。
俞小桃牽著女兒走了。俞小桃穿一件素雅的旗袍,半高跟的玄色皮鞋,把石板路踩出一串洪亮的響聲。
小葛很觀賞地看著俞小桃窈窕的背影,禁不住小聲道:“精致。”
段文船的眼“你為什麼這麼討厭媽媽?”她傷心欲絕,沙啞地問自己七歲的兒子。七歲不算太小,不可能無知,她是他的親生母親。睛包養網沒有落在俞小桃“精致”的背影上,而是靈敏地發明了小葛向里側挪了小半步——那挪近的小半步是和俞小桃在門臺上遭受的一霎時完成的。在俞小桃牽著女兒分開時,又挪歸去了,堅持了本來的間隔。段文船感到女人真是又心細又敏感,那不經意的或特殊經意的小半步,那離他近一點和遠一她在陽光下的美貌,著實讓他吃驚和驚嘆,但奇怪的是,他以前沒有見過她,但當時的感覺和現在的感覺,真的不一樣了。點的小半步,表達了多重的意味——接近時,是給俞小桃看的,或許是在領導俞小桃來對待他們之間的關系的——又挪回原地的小半步,才是她真正的的心態。段文船被小包養網葛應用了一下,感到很是好。
(本文節選自2023年第3期《芙蓉》中篇小說《仙草》)

陳武,江蘇東海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文學創作一級。曾在《國民文學》《中國作家》《十月》《作家》《鐘山》《花城》《海角》《芙蓉》等雜志頒發文學作品,多篇小說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中漢文學選刊》《作品與爭叫》《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等選載。